【48812】《广州文艺》选读丨陈世旭:广州三记
白云山在广州市北,几十座山峰簇集,主峰摩星岭,海拔不过四百米,是广州最高的山峰,浮在城市楼房波澜雄壮的浪涛上面。
旅行宣扬沿用着通行的方式:白云山早在广州建城之前的远古就闻名于世,战国名士收支,晋朝道士炼丹,南梁禅师建庙,唐朝就是旅行胜地,宋代以来每次评选出的“羊城八景”中有“景泰归僧、蒲涧濂泉、白云晚望、白云松涛、云山叠翠”,如此。
广州真实以恢宏雄壮的气势进入国际视界,是近现代的工作。至今,广州五次被《福布斯》评为我国大陆最佳商业城市第一位,联合国陈述的广州人类开展指数居我国第一。
即使如此,以我旅居十余年的经历,广州并没有失掉日子化、自然化甚至贩子化的尘俗韵致。
广州始建于公元前214年。商代称“南越”,周代称“百粤”,《汉书》称“南粤”。古民在古番山和禺山,筑“袤四里”小城,是最早的广州城。
城市传说的主角是最朴素的羊和谷穗:周朝时广州比年灾荒,五位仙人骑五羊从南海驾云而来,羊衔五色稻穗赐予大众。
广府粤语、一般话、客家话以致英语,皆有盛行;柱式门廊、柚木门窗、小院子,印证着多元文明的并存;避雨防晒的骑楼,门廊串联成廊道,沿街打开;“食在广州”无可争议:我国各大菜系、民间美食以及西方食谱,融会贯穿;早间问好,多是“饮咗茶未?”——早茶能够“直落”午后,亲朋团坐,如火如荼;新年插桃花“行桃运”、摆年橘“图吉祥”、派红包以“亨通”;船民祭拜的海神,是渔家的妈祖……一般的欢欣高兴,充满了焰火气味;结壮的日终年月,不张扬,不夸耀,不骄贵。
没有峻峭壁立的巉岩,没有触目惊心的峡谷,没有高不行攀的巅峰,没有装腔作势的仿古楼阁,没有怀旧自恋的府第遗址,没有惟我独尊的富豪别墅。一如粤地乡下到处能够邂逅的村民,你随意什么时间都能坐下歇脚,畅饮主人用药材煲制的糖水或凉茶,听他们叙说祖上的来历,村子的变迁,在城里打工、上学或经商的儿子女儿,忘却一路的疲乏。
亚热带滨海,温暖多雨,光热足够。四季常绿、花团锦簇的“花城”,年均气温缺乏二十二摄氏度,是我国年均温差最小的大城市。而白云山因其地舆上的优势,对城市生态构成极佳的调理,是广州的“市肺”。
一座体量巨大、气候富有、人口稠密的现代都市,有这样一座山,的确是一种福祉。
白云山有快捷的现代交通。缆车、电瓶车一应俱全。但除了老幼与外地旅客,当地人更多挑选了步行爬山。
从飞鹅岭下绕过旖旎麓湖,深化云台花海,自鸣春谷踏上石阶,一步步走出喧哗的尘嚣,一阵阵谛听城市的呼吸,一次次感觉身心的淘洗。在涨满谷地的花的激流中徜徉,在密林的缝隙里看阳光照射鸟雀的跳动。沟底泛青的古木,似乎丢失的陈旧歌谣。半山的平畴,儿童遥控无人机。无主的废园,老者沉吟陈年旧事。空谷的清风拂面,谁在耳旁悄然叮嘱:去搭白云的马车,去摘幻想的星星,把一种轻松的心境,在六合间随意挥洒。
摩星岭在不知不觉间呈现。岭上只要一个地舆标高,还有护栏铁链上很多的爱情锁同心结。
白云山的价值,或许正在于它的陡峭、素净、减弱,无须借势或有或无的名人,无须假造浅薄粗鄙的神话,无须堆砌假冒伪劣的古玩。
山给予了灵秀,水孕育了风味,白云山好像一个安静的处子,掩藏万种风情,给人以无量的幻想。
山不在高,水不在深。不用有仙,不用有龙。何必求名,何必问灵?满山的翠绿,就是人生的沃野。低处的人们,总想攀缘高处;高处的流水,总在去往低处。天上的日月,永久仰望人世;山下的草木,始终保持谦卑。很多向上成长的生命,才捧起了高远的天空。
白云山登高,是一种性灵的开释。雾恬淡,坡陡峭,松懈地散步,是极大的享用。品尝一种豁然,做一个轮回的梦。已然山之后仍是山,已然雾之后仍是雾,那就镇定自若,面临每一段旅程之后的旅程。
广州有花城之名。小时候从课本上读到长辈作家描绘的广州,皆不出一个“花”字。
咱们发现那里是花山,也是人海。在鲜花和绿叶堆成的一座座山下,奔流着汹涌的人群,咱们走入春天的最深处了。(冰心《记广州花市》)
买了花的人把花树举在头上,把盆花托在肩上,那人流似乎又变成了一道共同的花流。南国的人们也真懂得赏识这些春天的使者。(秦牧《花城》)
古来国中,洛阳看牡丹,昆明曰春城,皆以花市名世。而“海丝”注册,番邦珍品最早移入,南国广州即以草香花韵,至百代罕有对抗。曾被视为“化外荒蛮”的广州,虽风俗土俗有异于华夏,但由于岭南夏无盛暑,冬无寒冻,雨量充沛,土壤润泽,有利地势得天独厚,以致树木常青,繁花长盛。说什么岁枯月荣,广州花事无年月,此花才谢,彼花已放;说什么伤春悲秋,广州花事无春秋,此叶方落,彼叶已绿。
花市者,广州俗称“花街”。钩沉史籍文献,寻找“花街”芳踪,已二千余年矣。
西汉陆贾使南越,叹广州的“彩缕穿花”为观止。南越王赵佗因思乡,令城内广植陆贾自西域带来的素馨。夏时怒放,满城如雪,馨香充满。女子以彩丝贯之,素馨与茉莉相间,以绕云髻,是曰“花梳”;疍娘以花串悬于船周,装修装点;素馨提炼香油,儿女以脂面润发,冶以龙涎香饼,则神韵愈远;七巧节,珠江素馨花艇游泛。千门万户,皆挂素馨灯,结为鸾凤诸形,或作流苏宝带。豪门饮宴酒酣,出素馨球以献客,客闻寒香而陶醉以醒。挂复斗帐,能除夏炎,枕簟为之生凉。故此粤以素馨为矜类之尤物,蔚成风气。
素馨以其皎白可人,备受喜爱,名列花市第一。以素馨花为主的广州花市,最早有文字记载的在南宋。《岭外代答》(南宋·周去非)载,广州素馨花开时“旋掇花……以竹丝贯之,卖于市,一枝二文,竞买戴”,广州因称“天香茉莉素馨”。当年的珠江南岸,“平田弥望,皆种素馨”(《广东新语》),不啻为大花园。农家多以莳花、卖花为业,是故清诗人有诗“三十三乡不少,相逢八成花农”,《番禺县志》载:“花客涉江买以归……城表里买者万家,富者以斗斛,贫者以升,其量花若量珠然。”“花田一片光如雪,照见卖花过河。”(清·何梦瑶《珠江竹枝词》)足见其产销两旺。
其实早在唐时,广州就有了专门卖花的营生。唐末南汉,广州近郊即现卖花的花墟。
明朝中期,终年花市构成。《南越笔记》中载:“广州有花渡,在五羊门南岸。广州花贩每分载素馨至城,从此登舟,故名花渡。”
花码头,秋波桂楫木兰舟,红妆障日影悠悠。悠悠一水不行即,谁不怜花似颜色。钗头玉燕亦多情,不爱明(宝)珠爱素馨。君不见卖花儿女钱满袖,春风齐入五羊城。(清·方殿元《羊城花渡歌》)
明朝,广州莳花已成专业,从江南逐渐扩展到花地。清代的名作家沈复在其名著《浮生六记》里专门写到“花地”:“对渡名花地,花木甚繁,广州卖花处也。余自以为无花不识,至此仅识十之六七,询其名有《群芳谱》所未载者。”可见花地花市之盛。每年阴历正月初七,仕女结伴游花地,为其时习俗。平常花开时节,亦裙履联翩。俗谚“想死易过游花地”,“死”乃“挤死”之谓,是花地大策花市元宵灯展的描写。光绪年间,河南隔山名画家居巢、居廉兄弟,曾按二十四番风花信,写二十四种不同花的画册,使花地名花花容永驻。
乾隆年间,广州岁除花市逐渐老练,逐渐扩展到香港和东南亚。咸丰、同治年间,有了岁除花市。
岁除是花市的高潮。《广州城坊志》正式记载了岁除花市的盛况:“每届年暮,广州城内双门底卖吊钟花与水仙花,如云如霞,我们小户,售供座几,以娱岁华。”至此,广州花市已由单一的素馨花开展为多样化了,不光有吊钟花,还有水仙花。
广州人对花和花市可谓痴迷备至。即使是抗日战争时期,广州的岁除花市照旧举办。敌机腾空吼叫,市民照旧逛花市买花。花市一度不准的年月,几十年培养的数百名贵花卉种类毁于一旦,但广州人居家度日不行无花。村民自发“花墟”,市民轮渡而去,每次都在渡轮留下成堆被踩掉的鞋子。在广州人看来,花乃是六合赏赐,祥瑞而美丽,不行不敬,不行不亲。不准花市,逆天意,违民意。
20世纪70年代初,花市康复,规划逐年扩展。广州十大“岁除花市”,每天流量都达百万人次以上。
广州花市是我国绝无仅有的风俗景象,也是人间规划浩大的美色集锦,作为一轴散发着浓郁岭南风情的文明长卷,成果了广州“花城”的美誉。
一年一度的迎春花市,是广州人的嘉年华。但是,旅居广州十年,我一次也没有去过广州那些闻名的花市。
我所居楼下的纵横大街,每年岁除将近,便纷繁搭起了一排排展卖鲜花鲜果及年宵用品的竹棚,四乡花农海潮般涌来,层层花架沿街扩展,宛如巨龙占据,望不到止境。洛阳牡丹、漳州水仙、吉林君子兰、台湾蝴蝶兰、江西金边瑞香、欧洲薰衣草、泰国富有掌、荷兰郁金香、北欧玫瑰、南美五代同堂、比利时杜鹃……常见的茶花、芍药、月桂、玫瑰、含笑、海棠、蟠桃、大红柑、大红橘、四季橘、朱砂橘、金蛋果、代代果,以及广府新年必备的年花金桔、桃花和水仙,甚至再一般不过的鸡冠花……各式各样,目不暇接。街头巷尾,繁花漫漶,几被花海吞没。一切的首要收支口立起巨大的牌坊,灯光璀璨,气势壮丽。花市倒闭,摩肩接踵,风雨不透。
陈旧而又芳华的花市。灯色花光,春深如海。“人们挑选和安置这么一个局面来作为迎春的高潮,真是独具匠心。”(秦牧《花城》)
不过,当年秦牧先生赞赏的“一日之间广州遽然变成了一座‘花城’”,早已无须商讨。即使不逢岁除花市,广州也是家家有花、户户多彩,一年四季颜似锦。徜徉于千年古都,见的是一城艳丽,闻的是一城芳香,可谓无一日不是花市;实际中的广州,现代修建好像山岳,山山有绿植。浓荫葱翠,鲜花夹道,让粗暴有了妩媚,坚固变得温顺,可谓无一日不是花城。
广州人喜花、养花、赏花,一如他们的喜食、懂食、善食。食则山珍海味、花草果蔬,无所不能够入膳;花则天宫的仙芝、龙宫的琼瑶或不行得,无所不能够入赏。门前屋后莳花,堂上室内摆花,开业志庆送花篮,男婚女嫁坐花车,探亲访友捧花束……广州有最多的花店,借题发挥,触目可见;广州有最多的花景,远近凹凸,罕见空白。豪门巨贾不吝千金唯求国色天香,寻常人家一钵金橘、几株水仙清供岁朝。
“人无癖不行与交,以其无厚意也;人无痴不行与交,以其无真气也。”(张岱《陶庵梦忆》)依愚之见,鸟有鸟痴,鱼有鱼痴,石有石痴,木有木痴,广州多花痴。说花市是广州人的“独具匠心”,莫如说是他们的性格使然。
广州人的热爱日子,花是最靓的证明。花与广州人的日子志愿休戚相关,水融。广州人多质朴,务实惠,重名利。“讲意头”,成为共同的花言语:桃花寓红运;柑橘示吉祥;“发财树”“步步高”,其义自明;吊钟花“金钟一响,黄金万两”;标价数码多为“3”“8”“9”,谐音“生”“发”“久”,生猛、大发、持久;“行(hánɡ)花街”即“行大运”,广州本乡歌曲《行花街》唱道:
行花街咯喂,你本年梗位;行花街咯喂,你本年冇闭翳;行花街咯喂,你科科考最威;行花街咯喂,你高兴足一世;行花街咯喂,娶得一美妻;行花街咯喂,你先生变新贵;行花街咯喂,本年生番个仔!
广州人爱花,花也熏陶了广州人。花的招展使人单纯,花的芳香使人向善,花的斑驳使人唯美。
花是广州的标志,名头多与花相连:花都,花街,花市,花墟,花涌,花渡,花车,花舟……花是广州的手刺,人人皆是传花人;花是广州的盛宴,任人浪费春色。花是今天的喜庆,醉卧花丛君莫笑;花是明日的祝愿,家家抱得富有归;花是广州的方言,无花不言广州城;花是广州的气血,激荡着生命的生机;花是广州的魅力,吸引着国际的喜爱。
“争似莳花郎有幸,一成长伴佳人魂。”(清·陈坤《咏花田》)“花城”是广州的精魄,贮满的是美色。
“筠篮卖入重城去,分作千家绣阁香。”(清·张维屏《咏花市》)“花市”是广州的字号,买卖的是夸姣。
“千叶芙蓉讵类似,百枝灯花复羞然。”(隋·江总《南越木槿赋》)“花容”是广州的表情,展现的是永久的美丽。
广州陈家祠居闹市中心,宽广的广场前,大路如流,门庭若市。在很多树立的现代楼房中,建于清朝末年的陈家祠,仍然倔强地表现着其最初雄踞南粤的宏阔巨大、金碧辉煌。
1888年(光绪十四年),由数十位陈姓绅士建议,广东省七十二县的陈姓宗亲合资,在广州购买数万平方米房产,兴修合族祠,名“陈氏书院”,为全粤陈姓族员在广州备考科举、处理诉讼、交纳赋税等事宜供给居所。历时五年,于1893年(光绪十九年)完工。
“书院坐北朝南,主体修建面宽、纵深均为80米,平面呈正方形,为我国‘三进三路九堂两厢杪’院子式布局,由9座厅堂、6个院子、10座厢房和长廊巷组成,修建面积达8000平方米。院东新辟有1.7万多平方米的美化广场。”(拜见书院阐明)全体结构布局谨慎、真假相间,厅堂轩昂,院子宽阔。
书院修建的中心是中进大厅聚贤堂,当年族员在此举办春秋祭祀或议事集会。东西厅面宽三间,进深五间,梁架雕镂精密,屏风小巧玲珑,房顶陶塑瓦脊挺拔,堂前天台石雕栏杆嵌以铁铸的花卉。大堂昂扬深宏,柁墩斗拱抬梁,前后廊通堂木结构。双面镂雕屏门傍边,两边装设花罩。堂前有月台,石雕栏杆及望柱均以岭南佳果为装修,镶嵌铁铸通花栏板,颜色比照明显,装修华美,突出了聚贤堂的中心位置。
后进大厅三间是安设陈氏先人牌位及族员祭祀的厅堂。东西斋和厢房是当年书院的教育读书用房,斋内饰以花楣、隔扇和落地花罩组合,套色蚀花玻璃,斋前小天井,让室表里分外明亮清明。
书院修建以装修精巧、堂皇富丽而著称于世。来自岭南各地的大批能工巧匠会集广州,制造木雕、石雕、砖雕、灰塑、陶塑、铁铸工艺等各式各样的装修,遍及祠堂表里的顶檐、厅堂、院子、廊庑。
木雕。以浮雕和镂雕为主,是书院数量最多、尖端规划的修建装修。雕琢着难以尽数的前史故事和吉祥图画,可谓民间演员运用木头和钢刀雕就的前史故事长廊,是广东现存最大型的清代木雕创作。
石雕。首要是选用麻石石材。抱鼓石、石狮、月台、台基、墙裙、柱础、券门、垂带、台阶、栏杆、栏板及檐廊的檐柱、月梁、梁塾、雀替等易受阳光和风雨腐蚀的修建构件都选用花岗岩石材打造,其浅灰颜色与砖木结构修建的深重主调构成比照,彼此反衬,层次分明。聚贤堂前的月台是岭南石雕装修工艺的代表,交融了圆雕、高浮雕、减地浮雕、镂雕和阴刻等多种技法。大门前的一对石狮,石匠运用圆润简练的线条雕琢成形体生动、神态吉祥、笑脸相迎的瑞兽,是广东区域石狮造型的代表。
砖雕。以浮雕为主,部分选用透雕、圆雕、镂空雕。书院正面外墙上的大型砖雕,诗书画结合,是同期修建中罕见的大型砖雕;外墙檐下及廊门上的“挂线砖雕”边饰线条摆放规整,密布苍劲、纤细均匀,笔直如线。祠前壁间画卷式大型砖雕,每幅长达数米,立体、多层次的画面集神话传说、山水园林、花果禽兽、钟鼎彝铭于一身。演员按需布设图画纹饰,丰厚了单调的墙面,凸显了广东砖雕的风格,成为清代岭南修建砖雕艺术的代表。
灰塑。屋脊基座、山墙垂脊、廊门房顶、厢房和院子连廊及东西斋的屋脊,规划之大为岭南之冠。陶塑脊饰源自明末清初,盛于晚清,表现了南粤浓郁的民间修建装修风格。书院的正脊选用陶塑的数量和规划充沛显示出其时广东陈氏家族的经济实力。
铜铁铸和彩绘。连廊廊柱和月台围栏的栏板画蛇添足地使用了铁铸装修。民间演员奇妙地将铁铸通花栏板镶嵌在围栏的石雕结构内,使用铁和石之间的颜色比照以及铁铸的通透立体造型,使月台围栏产生出如国画斗方般共同的打扮润饰的作用,成为书院修建装修的一大特征。这些铁铸装修工艺,吸收西方的修建装修方法,结合我国的民间传统文明体裁元素,相辅相成,在清代传统修建中是较为罕见的。
一切这些修建装修,图画体裁广泛,造型生动传神,雕琢技艺精深,用笔简练粗豪却又精雕细琢,与宏伟的修建天衣无缝,作为我国现存尖端规划、保存最无缺、装修最精巧的祠堂式修建,陈家祠的“岭南修建艺术明珠”之誉,实至名归。早在20世纪20年代已为国表里修建专家和学者所注重,德国和日本的修建艺术专著中有专题介绍。
初进陈家祠,感觉不免震慑!十九座单体修建以聚贤堂为中心,其他按中轴线顺次布列,彼此间长廊连通,组成外关闭、内敞开的方式。门前坪地和东西后三院盘绕四周,与内部院子相应。长廊贯穿全院遮阳挡雨,房舍巨大阴凉透风降温,表里院子满目苍翠,高雅迷人,清凉而直爽。徜徉深深院子,穿过重重门廊,散步幽幽巷道,注视每一个房顶、每一片山墙、每一块雕琢,模糊间会觉得这儿的每一块石头、砖瓦、木块,都有自己的生命,灵动,跳动,透过前史,直击心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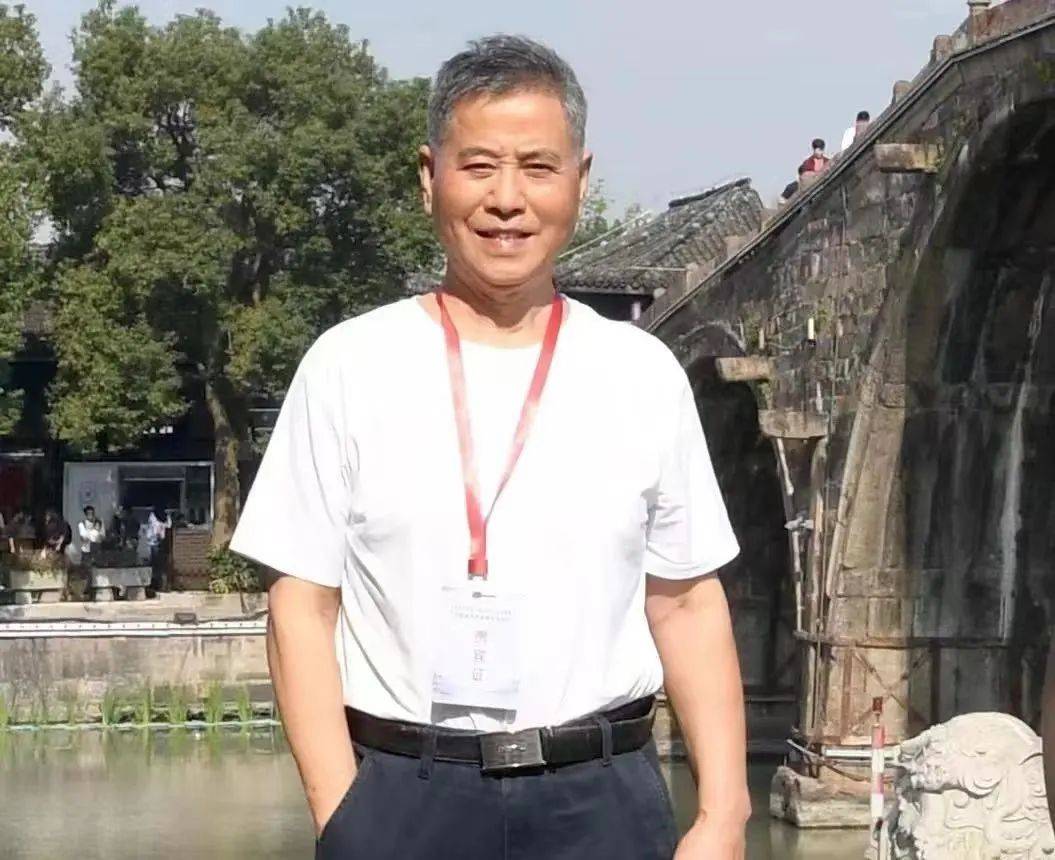
陈世旭,首届鲁迅文学奖获得者,曾任我国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我国作家协会主席团委员,江西省文联主席,江西省作协主席。现居广州。






